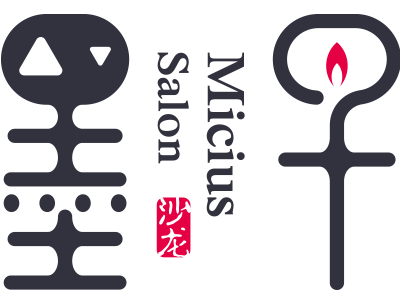本文于1987年7月14日发表于《纽约时报》,被收录在《数学百年风云:〈纽约时报〉数学报道精选(1892-2010)》。1987年是拉马努金诞辰100周年。
来源 | 返朴
撰文 | 詹姆斯·格雷克
翻译 | 凌浩
校对 | 林开亮
在某种意义上,数学家们最后都得去琢磨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1887.12.22-1920.4.26)的思想。
自从拉马努金1887年在印度南部库姆巴科纳姆的一座小城中诞生,时间已经过去了100年(编注:该文发表于1987年)。在他去世32年后,人们发现了他留下的一份奇特而原创的遗产:写在三本笔记本和一些草稿纸上的大约4000条公式。
拉马努金数学笔记中的两页
拉马努金在数学方面的能力与独创性,有些在他生前便为人所了解。与他同时代的人从那些涂满了定理的纸页上窥探到,他有一种天赋,可以计算出掌控着大量数字关系背后的定律。
但拉马努金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数学教育,在他多产的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他因地理因素而与世隔绝。他的公式常常深奥隐晦而又简洁优雅。他在自己的世界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工作,远离他所在时代的数学前沿,书写着内心看到的公式与定理。
如今他的研究早已进入了数学与科学之中,且远比从前那个时代所能想象到的更深入。具有可做代数运算的特殊程序的计算机使更多普通数学家可以更容易地追寻他的思想轨迹。从宇宙学的超弦理论到复杂分子系统中的统计力学,现代物理也发现它正越来越频繁地借助于数论和复分析的纯粹发现——这正是拉马努金的世界。
所以研究者们正在加速数学法医学和数学考古学的进程,以钻研这些未完成的文档,努力理解这些公式并证明它们。随着他们对拉马努金选择特定方法的原因了解得更多,他们感觉到有一个基础至今尚未被揭示。
“在他凭空变出这些非凡的东西时,它们不只是珍品,更是真理。”位于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的达尔豪斯大学的乔纳森·波温(Jonathan M. Borwein)说。与众多数学家一样,他发现自己近来一直借助于拉马努金的公式。“它们是某个暗藏的理论的证据,那些证据难以捉摸,他从未阐明。”
所谓“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也许是出于必要,也许是出于习惯,拉马努金的工作方式令现代数学家既崇敬又感到挫败。他在一块石板上匆匆记下公式,用肘部擦掉,再记下更多,直到算出最终形式才在他珍贵的笔记本上写下结果。
至于中间的种种环节,它们都丢失了。和主流数学家不同,他认为正确的结果不需要证明。他的遗产简单来说就是一组发现。
“对事物的感觉”
“他看上去在以一种与我们所知的任何人都不同的方法发挥着作用。”波温博士说。“他对事物有一种感觉,它们从他的脑中涌出,大概不管以何种可以翻译的方式,他都没有发现它们。这就像是在一场你从未被邀请的筵席上见到某些人一样。”
因此,数学家们花费多年——通常还是宝贵而多产的几年——来证明拉马努金知道的定理必定正确。推导那些公式往往比公式本身更有启发性。数学的分支学科围绕着拉马努金放置于独特环境中的构想繁盛兴旺。
在他的百年诞辰之际,数学家们聚集在美国与印度的会议上讨论拉马努金的研究所带来的意义。比起从前,他们有更多的原始材料需要研究,因为在上个世纪,投入到寻找和拼凑遗产中那些文档的努力已经有了新的结果。
伊利诺伊大学的数学家布鲁斯·伯恩特(Bruce Berndt)已经花费了数年时间编辑这些笔记,搜寻它们的来源及其关系,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多地证明那些未被证明的定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数学家乔治·安德鲁斯(George Andrews)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研究所谓“遗失的笔记”——拉马努金在他生前最后的一年留下的130页手稿。
“在快要去世的那一年里,他的工作相当于一个伟大数学家一生的工作。”威斯康星大学的理查德·阿斯基(Richard Askey)说,他曾与安德鲁斯合作,试图理解拉马努金的部分工作。
“他的成就令人难以置信,”阿斯基博士说,“如果这在一部小说里,没人会相信。”
如果拉马努金从未在1912年到1913年间给英国数学家写一连串不顾一切的大胆无畏的信,他也许会彻底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当时他25岁,在失业几年后做着一份年薪30美元的职员工作,但仍不愿将他的石板与公式丢在一旁。
他的家族在印度,地位很高,但很贫穷。在他之前,他的祖父与父亲在同一家布店做小职员。拉马努金有幸在库姆巴科纳姆接受了良好的中学教育,在那儿的图书馆发现了一些过时的二流课本后,他便开始了对数学充满创造力的探索。
“一个不知名的印度职员”
他的才智显著过人,但在他的出生地以北约240千米的马德拉斯的一所学院里,拉马努金在其他科目的考试中一次又一次不及格。在数学方面,他并没有老师。用英国数学家戈弗雷·哈代的话来说,他在“对现代欧洲数学家的完全无知”中学习。
哈代不是第一个收到来自这位“不知名的印度职员”来信的数学家,他回忆说:“充其量,就是个接受了一半教育的印度人。”但他却是第一个清楚这封信的意义的人。
拉马努金的信上说,“实际上,我知道接下来……而且我还知道……另外提一句,我发现了这个。”他列出了经过仔细选择的他的定理,多数是以恒等式的形式——陈述一些常见的量(如π)和一些不常见的量相等,或是两个不常见的量相等。
哈代带着困惑检验了它们。有少数令他吃惊,他后来说,他还认为自己也曾证明过部分相似的结论。他觉得有些定理,如果努力,他也可以证明出来——他确实做到了,但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另外一些定理是已知的。然而仍有一些,则“彻底难倒了我”。数年后,哈代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谈道。
剑桥之行
“我从没见过什么像它们那样,”他说,“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只有最厉害的数学家才能写得出来。它们肯定对,因为如果它们不对,没人能有这样的想象力创造出它们。”
另外,哈代还能断定,拉马努金有所保留,只提供了定理的特例,他敢肯定拉马努金还发现了更为普遍的版本。他安排发出了一封到剑桥大学的邀请函,1913年,拉马努金离开妻子到达了这里,一待就将近6年。
两人经常合作。哈代记得拉马努金很瘦弱,中等个头,眼中闪着光芒。拉马努金是个严格的素食者,所有的食物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做,当拉马努金在1917年莫名生病时,哈代认为是他的素食主义导致了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同样的迷恋
若干年之后,哈代花费了一番力气才消除了某种观念,也许是出于一种微妙的英格兰种族主义,人们认为拉马努金有一种亚洲风格的好奇心——要么是个“受神灵启示的白痴”,要么就是“古老东方智慧的一种神秘的表现形式”。与此相反,在哈代的眼里,拉马努金是个深思熟虑的理性主义者,很敏锐,但其中的宗教特性远远赶不上导致他离去的饮食习惯坚固。
他们都对数字迷恋,仿佛数字是活的,就像故事里的人物。他们思考整数,将整数分解为小因子,如300可写成2^2×3×5^2。他们研究一些问题,比如从严格的数学角度探究这些数字是如何常见,以及一些其他更难用语言描述的难题。
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
“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
拉马努金生病后的一天,哈代乘出租车去看望他,并跟他抱怨出租车的车牌号非常无聊——1729,只能写成7×13×19。“不,其实它很有趣。”拉马努金回答说。“在所有能用两种方法写成两个立方和的数中,它最小。”(1729是1^3与12^3的和,也是9^3与10^3的和。)哈代对拉马努金的理解与欣赏要胜过同时代其他任何的人。但即便是他,也无法免除时代与地域的有色眼镜。对他来说,拉马努金的故事最终是个悲剧——不完整的教育和无人指引的天才。当他最终评价这个年轻数学家的工作和他的课题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时,他表示失望。
“它们不具有伟大工作的简洁性与必然性,”哈代在1927年写道,“如果它们不那么奇怪,会更好。”
如今,几乎没有数学家能同意这样的评价,这些奇怪的结果迎来了光明,而哈代则退出了拉马努金的伟大光环。
“拉马努金晚出生了100年,哈代觉得这是个遗憾。”阿斯基博士说。那是个属于公式的伟大时代,是欧拉和高斯这样的数学家做出奠基工作的时代。“可我认为拉马努金没能晚100年再出生才是个遗憾。”阿斯基博士说。“我们在尝试解决一些变量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更难了,如果有人能有他那样的直觉帮助我们,一切将会变得不可思议。”
但他的直觉也并非永远正确。拉马努金也犯过一些错误,他曾声称发现了一个公式,根据这个公式,可以得到小于给定数的素数个数的近似值。但是,这样的公式并不存在。他过于乐观,早期时候他一直很乐观。在19世纪之前,数学家们便知道有些问题永远无法解决,但拉马努金孤立的生活使他远离他们的怀疑,正如远离他们的知识一样。
1919年,拉马努金病得更重了,在一家私人疗养院和一些疗养所之间几经辗转后,他回到了印度。他继续狂热地工作,和病魔斗争,在他能找到的任何纸上做计算。在接下来的那个四月,32岁的时候,他去世了。
1976年发现的论文
他在最后一年写下的130页未标记的手稿被保存在了剑桥三一学院的图书馆,和各种账单与信件一起放在一个盒子中,直到1976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安德鲁斯博士发现了它们。这就是“遗失的笔记”。
“把这个词用于在英国的一所重点大学的图书馆里发现的东西上有些古怪,”波温博士说,“但对那些了解其内容的人来说,事实就是如此。”
安德鲁斯博士发现,拉马努金在数学家们半个世纪都无法切入的问题上找出了一条道路。许多发现都关乎一个恒等式家族,他称之为仿θ函数——“算术方面的简单断言”,就如安德鲁斯博士所说,然而“它们的涵义非常深刻”。
“拉马努金花园”里的种子
正如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最近拉马努金大会上所说,这些数学帮助推进了理论物理中一个新的重要概念——超弦理论。“作为纯粹的数学,它和其他任何一朵拉马努金花园中成熟的种子所开出的花儿一样美丽。”他说。
另一个恒等式去年被用于在计算机上计算π的小数点后数万位。它收敛于某个精确值的效率比先前任何方法都高。然而,一如既往地,拉马努金仅仅是断言了他的发现。直到后来波温博士和他的哥哥彼得·波温(Peter B.Borwein)严格地证明了小数点后那些以百万位计的数字确实就是π。
拉马努金那些神奇公式的运用让数学家们猜测他当时正发掘一个埋藏很深的理论的脉络,它的全貌至今不明。但许多人并不愿细想拉马努金究竟是怎样进行思考的。
哈代注意到了拉马努金的出身,并发现了与欧洲社会隔绝的不完整的教育系统对他的严重忽视。尽管如此,如当今数学家们所意识到的那样,拉马努金上过一所像样的高中,些许书籍和文化传统使他渴望成为一名学者。
人们时常在他短暂而丰富的人生中寻找着经验教训,他们认为那些在如今这颗星球上十分缺乏。
“拉马努金的重要,不仅仅因为他是一名数学家,而在于他告诉了我们人类大脑可以做到何种程度。”阿斯基博士说,“有才华的人如此稀少而珍贵,我们不能失去他们。天才可以出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关于π的神秘公式
数学家们发现,拉马努金的许多公式既优美又晦涩。让他们惊讶的是,有个公式提供了一个极快速的方法来计算π值这一古老的课题。就在去年(编注:指1986年),一位计算机科学家运用拉马努金公式的某个版本将π计算到了17 000 000位。这之后,数学家才能证明拉马努金的见解为何是正确的。
本文经授权取自《数学百年风云:〈纽约时报〉数学报道精选(1892-2010)》,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关于“墨子沙龙”
墨子沙龙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主办、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协会及中国科大新创校友基金会协办的公益性大型科普论坛。沙龙的科普对象为对科学有浓厚兴趣、热爱科普的普通民众,力图打造具有中学生学力便可以了解当下全球最尖端科学资讯的科普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