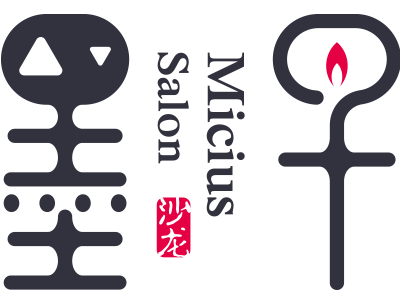哥廷根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和波恩教授强大的团队让我如鱼得水,继续寻找着新的量子理论。玻尔先生在1913年提出的量子理论模型是假定电子在原子核外固定的轨道上运动,在这个轨道上不辐射能量。电子从一个轨道跃迁到另一个轨道的时候会吸收或辐射一个光量子,两个轨道之间的能量差即为这个光量子的能量hv。玻尔的理论一开始就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无法用含时的方程来描述这个轨道之间的跃迁过程。还有一个致命问题,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组,电磁波(光)是周期的,那么玻尔模型中一个绕核在固定轨道上运动的电子所能辐射出的光的频率,必须是这个电子绕核运动频率(即绕核运动周期的倒数)的整数倍。这就引起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在量子数为m和n两个轨道上, m和n两轨道间跃迁释放的光量子能量hv(m-n) 要等于能级差E_m-E_n,同时频率v也要近似为m轨道和n轨道频率的整数倍。这只在m和n都很大,且m-n非常小的时候成立,在其它情况下,玻尔模型就无法自圆其说。

1924年的海森堡
究竟微观世界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才能准确描述?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1925年6月,我不幸染上了花粉病,即一种对粉尘强烈过敏的鼻炎。我选择了这个夏天去北海上的一个小岛Heligoland上度假,让清新的空气和温暖的海风给回我健康的呼吸,同时不断地思考着新的量子理论的突破点。
爬山,读诗集,加上思考量子理论成了我在小岛上宁静生活的全部。拿着这两年其它物理学家发表的大量光谱实验数据(不符合玻尔模型的预言),我在尝试着用新的模型来解释它。某一天的凌晨,我突然发现如果经典力学中成对出现的力学量符合一个非对易的关系,譬如坐标和动量符合 [x,p]=xp-px≠0,某些计算可能会得到和实验相符的结果。It was about three o' clock at night when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calculation lay before me. At first I was deeply shaken. I was so excited that I could not think of sleep. So I left the house and awaited the sunrise on the top of a rock that jutted out into the sea.——Heisenberg 1925
我在想着玻尔的模型中电子的轨道是一个圆,索墨菲老师将这个模型做了改进,使电子的轨道是一个椭圆,那我们真正能从原子中观测到什么?无非是通过它吸收的光和辐射的光来反推电子的动量和能量,而不是它的轨道!如果坐标和动量是非对易的,那电子显然就不会有固定的轨道,是不是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回到哥廷根,我就马上给在汉堡大学做助教泡利写了信,告诉了他我的想法。泡利是我最信任的师兄,他在去年提出了著名的“不相容原理”,即一个轨道上最多只能占据两个同能量的电子,而这两个电子在外磁场中一个会增加能量,一个会减低,从而区分开到不同的轨道上,使每电子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唯一轨道,因此核外电子有了壳层结构。他被誉为物理学界的奇才。
此时,我告诉他正酝酿着一个比他的工作更重大的计划,我想摒弃玻尔模型中电子轨道的概念!
Everything is still vague and unclear to me, but it seems as if the electrons will no more move on orbits. All of my meagre efforts go toward killing off and suitably replacing the concept of the orbital path which one cannot observe. ——Heisenberg, letter to Pauli, 1925
这个idea尽管很疯狂,我还是把他写成了一篇论文,交给了波恩教授。我的出发点是把描述经典周期系统的傅里叶级数做一些改变,因为原来的傅里叶级数不会产生新的频率,而原子中能级间的频率由于可相加,即v_m-v_n= v_m-v_k+ v_k-v_n,新的级数自然要包含这个性质。原子系统产生E_m-E_n跃迁时只跟这个频率(E_m-E_n)/h共振,于是和这个跃迁相关的新的傅里叶级数的系数q_{mn}只包含这个频率,并且q_{mn}=q *_{mn},该系数即满足一个含时的运动方程q_{mn}(t)=exp{2\pi i(E_m-E_n)/h} q_{mn}(0)
于是广义坐标X_{mn}和广义动量P_{mn}的乘积可以写成两者新的傅里叶展开系数的乘积,即XP_{mn}=\sum{k=0}^{\infty}X_{mk} P_{kn},这样即可以满足频率相加,同时满足非对易关系XP_{mn}≠PX_{mn}。一个量子系统的哈密顿量H就可以用这种新的广义坐标和广义动量来表示
The present paper seeks to establish a basis for theoretical quantum mechanics founded exclusively up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quantities which in principle are observable.
--Heisenberg, summary abstract of his first paper on quantum mechanics
玻恩教授看过我的论文后,第一时间鼓励我发表,并思考几日告诉我一个重要的idea:我用的这种傅里叶系数可以用矩阵来表示! 在玻恩教授的鼓励下,我的paper首先得以发表:【W. Heisenberg, Über quantentheoretische Umdeutung kinematischer und mechanischer Beziehungen, Zeitschrift für Physik, 33, 879-893, 1925】,随后玻恩教授马上和帕斯卡.乔丹合著了一篇用矩阵来描述我的理论的paper: 【M. Born and P. Jordan, Zur Quantenmechanik, Zeitschrift für Physik, 34, 858-888, 1925】,很快在年底之前,我们三人合著了第三篇paper: 【M. Born, W. Heisenberg, and P. Jordan, Zur Quantenmechanik II, Zeitschrift für Physik, 35, 557-615, 1925】,正式宣告量子力学的第一种形式——“矩阵力学”的诞生。
文中我们的矩阵力学建立在这几个假定上:
1.所有的物理量均用厄米矩阵表之。一個系統的哈密顿量H是广义坐标矩阵X和广义动量矩阵P的函数。
2.一个物理量Q 被观测到的值,是该矩阵的本征值Q_{mn} 。系统能量 E_{mn}自然就是哈密顿量H的本徵值。跃迁频率v_{mn} = E_m-E_n。
3.物理系统的广义坐标矩阵X和广义动量矩阵P满足如下非对易关系,这是我们矩阵力学的核心:[x,p]=XP-PX=\frac{ih}{2\pi}*I, 其中I为单位矩阵。
泡利很快用我们的矩阵力学计算出了氢原子能谱,符合了所有光谱观测实验的预言!我们的工作点燃了整个物理学界,于是1925年成了玻尔量子理论的逝去,全新的“量子力学”的诞生年份。

海森堡(右二)和帕斯卡乔丹(右一)在1927年
接下来的1926年,我不断地受邀到欧洲各地讲述我们的矩阵力学。在剑桥大学,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博士生的提问引起了我非常浓厚的兴趣,他叫他问我是否想过非对易关系和经典力学中的泊松括号之间的对应,一个经典力学到量子力学完美的对应原理过度。我被他的发现所震动,知道了他叫保罗.狄拉克(Paul A. M. Dirac),一个瘦瘦高高,黑发深眼窝的哥们,比我小半岁,在我的工作启发下决定投入量子力学的研究,他使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竞争压力。

保罗.狄拉克
然而这一年,一个奥地利人的工作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从天堂到人间的落差。他叫埃尔文.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和玻恩教授年纪接近,是位风流倜傥的大叔,在苏黎世大学任教。传说中阅女无数,情人成排。上帝真是爱开玩笑,当年爱因斯坦提出光子假说的时候,玻尔教授不是很接受,所以在他的旧量子理论里还是习惯用经典的电磁波,没有在乎它的的波粒二象性。而一位法国贵族路易斯.德布罗意(Louis Victor de Broglie),郎之万的学生,在1924年提出了一个比较crazy的idea,将波粒二象性推广到了所有粒子当中。电子的波动性在1927年得到了实验证实,然而1926年薛定谔教授就大胆的用波来描述电子,让原子中的电子成为了在原子核库仑作用束缚下的一个波。他的理由是我们的矩阵力学太难懂,想自己构造一个直观的。于是他注意到了波粒二象性,而我们这帮人谁都没有注意到。
I knew of Heisenberg's theory, of course, but I felt discouraged, not to say repelled, by the methods of transcendental algebra, which appeared difficult to me, and by the lack of visualizability.——Schroedinger in 1926

埃尔文.薛定谔
薛定谔在这一年发表了他的波动方程:-ihd\phi /dt = H\phi,一个极其简单的形式。我怀疑他是用平面波带入\phi反推出这个形式,然后假定这个形式对所有的物质波都成立。我一开始也不太接受他的方程,甚至在给泡利的信里写了很悲观的话。
这一年的春天,我离开了哥廷根,离开了玻恩教授和内向的帕斯卡乔丹,前往我第三个老师,也是我一生的恩师玻尔教授那里做助教。没错,他就是那位巨人,我站在他的肩膀上开创了量子力学的巨人。我们真是命中注定的一对师徒,随着泡利的到来。从那一天起,哥本哈根成了量子力学的中心。玻尔教授的风格真是雷厉风行。他一直关注着我们在哥廷根的矩阵力学,一直给予我支持。于是当薛定谔方程横空出世的时候,他要弄懂我的矩阵力学和薛定谔的波动力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都能得到合理的结果?他马上把薛定谔请来了哥本哈根。不顾薛定谔发着高烧在床前和他讨论,真是疯狂。玻尔教授满嘴的state,薛定谔满嘴的wave,乍听上去真是鸡同鸭讲。薛定谔回去后,终于发现了他的波动力学和我的矩阵力学是完全等价的,一个是态随时间变化而力学量不变,另一个是力学量岁时间变化而态不变。区别就是随时间变化的因子exp(iHt)是写进我的力学量算符里,还是写进他的波函数里。1927年,我们在哥本哈根的主要工作是给量子力学建立一个严格的逻辑体系。泡利用波函数的反对称性质重新建立了他的不相容原理。在海峡的另一边,狄拉克整理着我和薛定谔的工作,提出了态矢量,算符,相互作用表象等诸多概念。他成了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量子力学体系的领头人,帕斯卡乔丹等人也参与其中。而我在读他们的paper时,一直在思考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考虑波粒二象性,那么对于一个平面波exp[-2\pi*i(px-Et)/h],非对易关系[x, p]=xp-px=ih/2\pi自动满足。是非对易关系直接来源于粒子的波动性?我发现了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原理作为桥梁,该原理课是非对易关系的直接推论,亦是粒子波动性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个原理就是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玻尔教授一直信奉互补原理,即一个物理系统要靠两个互补的力学量来描述。而我的测不准原理刚好是这对互补力学量之间的关系,如坐标和动量ΔpΔx≥h/2,时间和能量ΔEΔt≥h/2,即你不可能同时知道坐标和动量的精确值,也不可能同时知道时间和能量的精确值。测不准原理作为我们“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的一部分,遭到了很多物理学家的反对,包括我们一代人的偶像爱因斯坦。玻尔教授极力地维护着我们诠释,他和爱因斯坦长达多年的论战也就此开始。1927年的索尔维会议就是量子力学的庆功宴,物理学界的大牛们悉数到场。会议结束时我们的合影堪称经典,第一排坐着普朗克,居里夫人,洛伦兹,正中间的爱因斯坦,和郎之万等人,第二排坐着狄拉克,康普顿,德布罗意,玻恩,玻尔等人,第三排站着薛定谔。泡利等人,还有我。物理学史上恐怕难以找到第二张这样牛的照片了。
We regard quantum mechanics as a complete theory for which the fundamental physical and mathematical hypotheses are no longer susceptible of modification.--Heisenberg and Max Born, paper delivered to Solvay Congress of 1927

1927年索尔维会议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