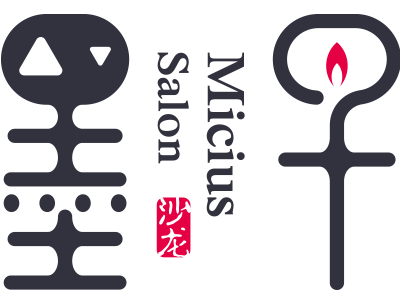在我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也就是1933一月,希特勒上了台,纳粹党开始执政,奥地利不久并入了德国,德意志正在悄悄的发生变化。这个国家尽管有非常多的诺贝尔奖得主,我却是最年轻的一个,渐渐地受到重视。作为莱比锡大学理论物理的唯一教授,我的队伍也不断地在发展壮大。作为量子力学的最早创始人,我不断地被邀请到世界各地进行讲学。然而这时,纳粹党徒开始对犹太人下手了。

希特勒上台
犹太人,作为一个被罗马帝国中东从驱散到欧洲,最后流浪到世界各地的民族,在智慧上有着其他民族难以比拟的优势。他们顽强,聪明狡诈,可以不信耶稣。他们是天生的商人和投机者,家家生活富足却饱受歧视。他们的财富使子女们获得了远高于欧洲平均水平的教育,于是培养了众多学者,尤其是理论物理学家们。普朗克先生、爱因斯坦先生、索墨菲老师、玻恩教授、玻尔教授、薛定谔、还有泡利,尽管他们血缘中可能融入了很多其他民族的成分,他们都是在典型的犹太家庭中长大,都可以称作是切切实实的犹太人。
我不明白希特勒为什么这么仇恨犹太人,在他上台以后居然颁布一系列的法令来限制犹太人在德国的权益,发动媒体攻击犹太人,把他们当二等公民对待。

普朗克与爱因斯坦

索墨菲与波尔

薛定谔

泡利

玻恩
斯塔克(Johannes Stark),曾经发现原子在电场中光谱频移效应而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老家伙,居然在报纸上撰文声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是犹太人的物理学,大肆攻击。普朗克先生年事已高,而且曾经位高权重,盖世太保们还不敢动他。爱因斯坦则不然,他十几岁便离开慕尼黑去了意大利,后来在瑞士成长并接受教育,提出相对论和光量子假说,在功成名就后才被普朗克先生请回柏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连半个德国人都算不上,却是个犹太人,于是他成了众矢之地。
爱因斯坦被逼走了,远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同样在柏林,接替了普朗克职位的薛定谔也被逼走了,去了爱尔兰。在哥廷根,玻恩教授也被逼走了,去了英国(帕斯卡乔丹不是犹太人,这个愤青果然不出我所料,加入了纳粹)。泡利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在德国的犹太裔物理学家们基本都被逼走了,何去何从成了我的问题。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给了聘请我去做教授。在慕尼黑,即将退休的索墨菲老师一心想让我接替他的职位。虽然我是日耳曼人,却和这些犹太物理学家们关系太过紧密,在那帮人眼里,我就是个白色犹太人(white Jews)。我该怎么办?是和大家一起逃?还是留下来接受这暴风雨的考验?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不能允许斯塔克这样的家伙如此祸害我的祖国,我要和他拼了。犹太物理学家们的离去等于毁掉了德国物理学的半壁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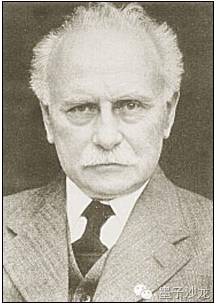
约恩纳斯.斯塔克
就这样,我被党卫军(SS)的头子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抓起来审问。凭借我母亲和他母亲的私人关系,以及我诚恳的为德意志第三帝国效忠的态度,经过一年的考察,我没有被驱逐,但是被告知不允许去慕尼黑接替索墨菲老师的职位。 Heisenberg is only one example of many others...They are all representatives of Judaism in German spiritual life who must all be eliminated just as the Jews themselves.--SS newspaper, 1937老师和朋友们的相继逃亡,纳粹对我管制和怀疑,让我经历了人生最低潮的几年。在这个时候,我结识了一生的挚爱,伊丽莎白.舒马赫(Elisabeth Schumacher),一个比我小14岁的姑娘,是莱比锡大学的学生。这些年为了物理学,我似乎远离了爱情的滋味,直到她的出现,是她陪伴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那段时光。我们很快相爱并在1937年结婚,从此她的名字变成了伊丽莎白.海森堡(Elisabeth Heisenberg),成为了我的妻子。她为我在1938年生下了两个孩子——是个双胞胎。泡利在心中恭喜我说这是个伟大的pair creation。

海森堡和夫人伊丽莎白摄于1937年
在这个风雨飘摇的30年代,物理学还继续发展着。自量子力学被我们创立之后,原子系统已经被它解决的很清楚了,我们开始向原子核进军!去探索这个世界更深层次的奥秘。剑桥的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卢瑟福教授(Ernest Rutherford)自1912年发现了原子核式结构后(即玻尔就量子论的出发点,玻尔老师曾在卢瑟福手下干过),1918年又发现了质子。1932年他的学生和继任者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在1932年发现了中子,他们师徒和狄拉克两人几乎代表了当时英国物理学的全部。狄拉克曾担心自己变得太出名,不想和我们一起去领1933年诺贝尔奖。卢瑟福劝他说如果这么做会让他变得更出名,于是狄拉克去了。
查德威克的小组和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的小组所做的一切现有的实验结果都表明,原子核里只有质子和中子两种粒子,于是我大胆地假设原子核就是由这两种粒子组成的,并且相信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由量子场论来描述。1932年我引入了一种同位旋(isospin)的概念来描述原子核内质子和中子间的对称性【W. Heisenberg (1932). "Über den Bau der Atomkerne". Zeitschrift für Physik 77: 1–11】。1935年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Hideki Yukawa)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第一个核力的量子场论模型,质子和中子间作用力靠介子传递。1937年维格纳提出了isospin这个词和它的SU(2)对称性。值得一提的是维格纳把他的妹妹嫁给了狄拉克,也许是当妹的太崇拜哥哥,没办法当哥的只能给她介绍一个比自己还强的物理学家。 原子核物理学和政治看似并行不悖地发展着,但是我的故交恩里克费米在意大利做的实验改变了这个局面。费米是我们这一代人里少有的实验和理论兼修的全才。他早在1926年就和狄拉克几乎同时提出了半整数自旋粒子的统计规律:费米——狄拉克统计,即和整数自旋粒子的玻色-爱因斯坦统计相对应的规律。他曾在玻恩教授手下访问过。1934年他在泡利的中微子理论基础上提出了β衰变的费米理论。在人工放射性被发现后不久,他实验演示了几乎所有元素在中子轰击下都会发生核变化,并能用重水里的氘原子核使中子速度减慢。费米的妻子是犹太人,他自然也受到牵连。为了躲避墨索里尼政府的迫害,他在1938年领取诺贝尔奖之际逃往了美国。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离去是对轴心国的最大损失。1939年,梅特纳夫人(Lise Meitner),哈恩(Otto Hahn)和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在发现了原子核的裂变现象,同时伴随着巨大能量的释放。一个可怕的概念出现了——核武器!
梅特纳夫人是犹太人,她先后在荷兰和哥本哈根玻尔教授那里躲避纳粹的迫害。而哈恩和斯特拉斯曼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他们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制造核武器的任务,而纳粹委派我去在理论上指导他们的工作。哈恩比我大22岁,他和爱因斯坦是同龄人。那个时候他是威廉皇家学会化学研究所的所长,我是威廉皇家学会物理研究所的所长。没错,从那一天起我海森堡和哈恩就成了纳粹核武器计划的领导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的海森堡和哈恩
1939年我的祖国,由希特勒的纳粹党执政的德国,开始闪电入侵波兰,战争就这么残酷地展开了。曾经在莱比锡,一个叫周培源的中国人慕名来跟我学习量子理论,他来了之后我的乒乓球水平从全校第一变成了第二。他经常向我们讲述着他的祖国在日本人的残酷侵略下殊死抗争的故事。没想到那么快,我的祖国开始残酷地侵略别人,而我们没有丝毫地负罪感,因为一战失败的伤痛一直伴随这和我们这一代人,西边的法国和东边的波兰处处地为难着我们,让我们食不果腹。因此我们这场战争我们起初的目的只有一个——复仇!

小编注:周培源(1902年8月28日-1993年11月24日)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
英法开始对我们宣战,昔日的好友成了敌对国。我和泡利,狄拉克,薛定谔,玻恩教授,查德威克等人就此断了联系。我们很快和苏联人瓜分了波兰。苏联人在卡廷森林杀尽了波兰精英并嫁祸给我们。希特勒尽管极力反犹,但是这几年的治理使德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高速增长,受到大家的支持。相比之下,斯大林更像是一个魔王,他上台后残害的忠良不计其数,连玻尔老师和玻恩教授的得意门生朗道都未能逃脱他的魔掌。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全面地开始了!披上这身军装,民族自豪感卓然而生。我们的军队三天占领丹麦,四天攻下荷兰。比利时人很快屈服并为我们开路,德意志帝国的装甲部队就这样绕过马其诺防线,在法国境内长驱直入,两个月征服了整个法兰西,凡尔赛和约的阴影在巴黎上空烟消云散,我们实现了复仇。整个欧洲大陆的残余抵抗力量都逃到了英国,凭借那小小的海峡负隅顽抗,胜利对我们来说指日而待。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欧洲的犹太人被我们的军队残忍地屠杀着。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是我们的盟友,尽管战斗力不值一提。西班牙的弗朗哥对我们言听计从。瑞士银行为我们洗着战争的黑钱,东欧斯拉夫人的那些地盘被我们全部占领。欧洲大陆只剩下另一个强大的国家——苏联,在我们的控制之外。 我始终不明白希特勒在1941年为什么要去突袭苏联,难道是胃口太大,对他那广袤的土地和丰富资源垂涎已久?但既然战争开始了,我们日耳曼人就要全力以赴,让整个欧洲都成为德意志的天下。复仇的快感的膨胀民族自信心渐渐地扭曲了我们的灵魂。
在常规武器主导的战场上,我们似乎无坚不摧。但是美国人也在研究着核武器,称为曼哈顿计划,跟我和哈恩的领导的组在竞争着。他们的阵容看上去更为强大:主负责人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是我离开哥廷根后,波恩教授的一个博士。我不太喜欢这家伙,因为在同位旋理论上他处处刁难我,这回他成了我的直接对手。曼哈顿计划理论部分负责人贝特(Hans Bethe),索墨菲老师的学生,也就是我的师弟,一个很强的家伙,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逃往美国。还有我在莱比锡的得意门生布洛赫(Felix Bloch)和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布洛赫也是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被驱逐。据说天才数学家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也加入了他们的理论部,后来我知道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叫费曼(Richard Feynman)的天才。曼哈顿计划实验部分负责人果然不出我所料,是费米!当然实验物理学家安德森(Carl D. Anderson)等人也参与某些秘密武器的研制当中,就是他在1932年发现了正电子,验证了狄拉克方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铀俱乐部,后排左5为海森堡
For the present I believe that the war will be over long before the first atom bomb is built. --Heisenberg, recollection of a statement in 1939
我们核裂变能源和武器的计划成为“铀俱乐部”。在一次次计算核裂变速率和一个链式反应炸弹所需要的放射性铀235时,我常常反问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作为一个长者,哈恩一直潜移默化地暗示我他的想法——战争该早些结束!哈恩用他的权利留住了很多犹太人化学家在他的研究所工作,他告诉我说无论战争多么残酷,我至少应该肩负起保留德国物理学青年人才的责任,不让他们白白地到战场上送死。 每周我都要往返于柏林和莱比锡之间,管理着我们的计划。我们希望能抢得先机,在美国人之前造出核能设备和核弹,这样美国人就不敢参战,苏联人和英国人会很快屈服,战争就会很快结束,更多的生命会存活下来。1941年9月,经过一层又一层的审核,纳粹终于同意我去哥本哈根讲学一周。我当然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在身——拉拢玻尔老师,为我们的队伍添上最重要的一个大人物。玻尔老师和我情同父子,在量子力学创立的过程中他曾是我们这帮年轻人的领袖。我来到了哥本哈根大学,那熟悉的小楼,熟悉饭厅,熟悉的海水和阳光。不同的是,我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玻尔老师也年近60,而他的祖国丹麦正被我的祖国的军队占领着。

1941年,海森堡和夫人伊丽莎白访问哥本哈根
那天晚上,我又来到了玻尔老师家中,和他长谈。我期望有如当年我们讨论量子力学那样的长谈,但是时间再也回不去了。玻尔老师表情凝重,因为我的祖国侵略了他的祖国,在全欧洲大肆地迫害着犹太人。我告诉玻尔老师我们的坦克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征服苏联指日可待,英国也快被我们炸平了,欧洲再没有力量能抵挡我们。您现在有两个选择,最好的选择是让这场噩梦般的战争早些结束少死点人,那您就应该加入我们,研制出核武器,这样战争就会很快结束了。玻恩教授走的时候我也被牵连,没有能力保护他,但是我现在身居要职了,我会用我的身份保护您,以及其他的犹太物理学家。尽管爱因斯坦和薛定谔都走了,柏林还有普朗克先生和冯劳厄(普朗克的学生,因发明X射线衍射技术获得19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样的您的故交。第二个选择是您可以通过英国人给奥本海默他们捎个话,让咱们双方都怠工,不造出核武器,这样战争会慢慢拖下去,也会少死些人。 玻尔老师非常不快,他知道我此行的目的还想要从他这里拿走同位素分离的小加速器,一心要为德国搞出核武器。很显然,第二条路走不通,我们和美国人互相都不会信任对方,至少在他们眼里,希特勒是个混世魔王,而美国的经济命脉被犹太人把持着。
玻尔老师告诉我说,我们只谈物理,不要谈这该死的战争。这场战争对于你们德国人是复仇般的宣泄,对我们丹麦是彻头彻尾的灾难,我不会选择与侵略者合作。我诚恳地告诉玻尔老师,我和伊丽莎白不敢想象我们的孩子像我小时候一样饱受战争失败的折磨,我希望德国获胜,越快越好,因此我会全力以赴地为国效力,发展核能和核武器。我们的谈判不欢而散,很多年后双方都不愿提起这一晚,我没能拉拢到玻尔老师,但还是想方设法地在盖世太保满哥本哈根抓捕犹太人时保护他。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不久玻尔老师就在当地反抗组织的协助下逃跑了,去了美国,加入了费米和奥本海默他们,我的信心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感觉到我的老师,朋友,和学生们都背离了我,去了美国人那边。

曼哈顿计划中的几位物理学家,左起玻尔,奥本海默,费曼,以及费米1942年冬天1942年冬天,我们的军队在苏联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苏联人保卫住了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开始向我们发动反击。同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惹恼了美国人,这个工业第一大国终于参战了,二战的天平开始倾斜。我不敢想象一旦我们和美国人都有了核武器,世界将变成什么样?是不是双方要同归于尽?
德国这边,我明显看到哈恩开始怠工,他用我们经费来裂变周期表上各种各样原子,而不是只钻研基于铀235的核武器。我慢慢地说服他,让他和大家都相信我,但是我做的初步计算结果发现,要产生核武器的链式反应,至少需要几吨的铀235,这在当时是不可能搞到的,美国人也搞不到。于是我长舒一口气,认为这个世界得救了。我没有检查我计算的结果,而是向希特勒他们直接汇报说核裂变只能作为核能,不适合做炸弹。1944年,我们在欧洲战场东西两线都遭受了失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我们腹背受敌,曾经占领的地方在不断地丧失,意大利这个不争气的盟友很快就投降了。柏林上空被盟军惨烈地轰炸着,苏联人也推进到了离莱比锡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伊丽莎白和孩子们的处境很危险,我不能再呆在这里了!我像哈恩他们匆匆道别,骑个自行车开始往南赶,一路上风餐露宿,看着我的祖国到处是被轰炸的痕迹,一片狼藉。在路上,我被疯狂的士兵劫了下来,枪口正顶在了我的胸口上,因为我穿着军装,被当成了逃兵。我掏出自己的通行证,却被他们扔在一边,我的性命栓在了他的扳机上。如果这个混蛋手指动一下,我就会像Majorana(意大利天才理论物理学家,费米曾经的助手,后来跟随海森堡工作)那样神秘地失踪,尸首无存。

Ettore Majorana
没想到我口袋里的那包美国香烟救了我的命,我递上它,这帮当兵的放我过去了。在这个残酷的战争年代,你的性命也许只值一包烟,他们不会知道眼前的人是海森堡,也不会去关心,战争失败的阴影笼罩着每个人。我逃回了莱比锡,将伊丽莎白和孩子们转移到了慕尼黑附近的一山区个小村庄,过起了短暂的田园生活,我等待着审判的到来。1945年1945年4月,德国战败,希特勒自杀,我的祖国被美英法盟军和苏联红军瓜分成大大小小的势力范围。1945年5月,我在家中被一小队英国特种兵静静地带走,俘虏去了英国。我和哈恩等我们参与纳粹核计划的重要人物人都被关在了这里。他们记录着我们的谈话。1945年8月初,美军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上空投下了两颗核弹,我们所有人都震惊了。哈恩他们质问着我的计算结果,我才知道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没有计算中子扩散率,因此大大夸大了所需要的铀235的重量。我重新计算一次,发现只需要几公斤。当然后来我才知道,费米他们还造出了钚核弹,美国人赢了,却用这个两个小炸弹瞬间屠杀了上百万日本人。 哈恩情绪出现了崩溃,说我是个二流的家伙,一流的家伙不会出现这种错误,然后为自己是原子核裂变的发现者而深感罪恶,不能自拔。今天核弹屠杀了这么多人,明天不知道又要屠杀多少。我依然在暗自庆幸,如果我计算对了,被毁的可能不仅仅是广岛和长崎,而是柏林,伦敦,巴黎,莫斯科。。。。至整个欧洲大陆。
1945年二战结束了,我们又一次成了战败国。我回到德国,和伊丽莎白以及孩子们在慕尼黑开始艰难的战后岁月。一切都变了,我们再也回不到战争之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