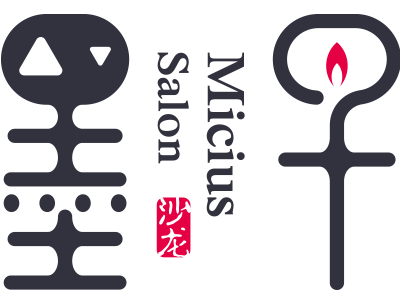小墨上回跟大家说到,科学家在尝试对基因缺陷进行治疗的时候,利用了病毒一种类似茅山道士穿墙而过一样的超能力,把遗传病患者细胞体内缺少的正确基因补上,来达到产生正确蛋白的目的。由于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局限,这种传统的基因治疗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瓶颈,科学家开始寻找更好的办法。
科学家们是这样想的,既然是基因出现了错误,那么我们可以对基因动手术啊,哪里坏了点哪里,把错误的剪下来,把正确的放进去,不就万事大吉了?这种剪切、删除、替换的过程,就类似对DNA序列的编辑,所以,人们管它叫做“基因编辑”。
没错,三步:第一步,找到错误的碱基片段;第二步,用剪刀把错误碱基“咔嚓”一下剪掉;第三步,把正确的碱基放进去,和前后的碱基拼接好,形成完整的DNA链。So easy!哈哈哈~

不过,老祖宗教育我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基因动手术,工具在哪里?找到错误碱基需要GPS定位器,剪掉错误碱基需要剪刀,拼接正确DNA需要针线。而这些精密操作还必须要在极其微小的细胞内部,还得对相当数量的细胞做操作才能起到效果。这样的工具到哪儿去找呢?
向大自然去找!在寻找这些手术工具的故事里,写满了人类和自然界万千物种互通有无的段落。想着向大自然寻找答案,不是“有枣没枣打三竿”的盲目之举,而是科学家有的放矢的探索。我们知道,对于高等生物来说,每个细胞里面的DNA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但不同种类的细胞却显现出截然不同的功能。那么,是什么机制决定了细胞中哪些部分得以表达呢?一定有一种准确的GPS,负责特定基因在合适的时间场合进行表达。
人们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摸索,就是为了寻找高效、准确的工具,事实上,给我们最大启发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高等生物,恰恰是最不起眼的细菌和病毒。
说细菌和病毒不起眼其实真的是不公平,因为我们的生活根本不可能离开它们。比如小墨平时爱喝的酸奶,还有春天的味道——腌笃鲜里面的火腿,就都离不开这些微生物的辛勤劳动。
说到酸奶,和咱们今天的故事有很深的渊源。
1987年的时候,科学家发现大肠杆菌的DNA序列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有一段由29个碱基构成的序列重复出现好几次,彼此之间被一些没什么规律的序列隔开。好像用绳子串起来什么重要信息。但是当时,科学家完全看不出这个结构有什么作用。要知道,由于“身体”特点所限,细菌的基因本就不复杂,它真的会拿出宝贵的序列资源,却对自己毫无用处吗?
好吧,姑且认为这段重复序列是因为大肠杆菌没有把无用片段进化掉,是偶然现象好了。万千世界,什么事儿没有啊。当时,科学家给这种序列起了一个直观的名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这就是现在让人听了心中一凛的词儿——CRISPR。只不过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几个字意味着什么。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也许这些重复碱基片段就是他丢给人类的密码,他会得意地看着人类下一步要如何解开谜底,然后为自己的鬼斧神工惊叹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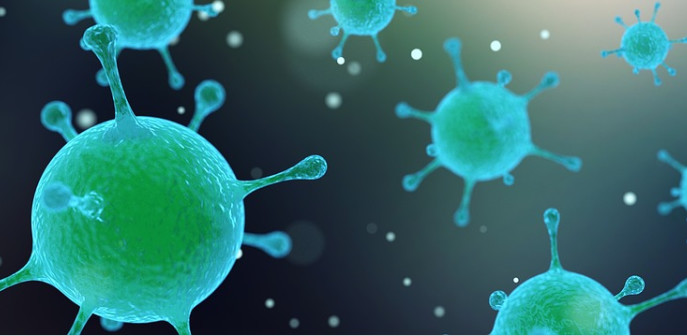
可是几年、十几年以后,类似的现象又陆陆续续在不同的细菌中发现。对于任何生命体来说,生存和繁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调动极其有限的资源完成遗传物质的保存、复制和表达。怎么可能这么多细菌都齐刷刷地那么愚蠢,浪费这么有限的资源,啥都不干呢?
更神奇的发现还在后面,有那么一些负责连接重复片段的DNA(就是前面说到的连接神秘重复序列的“绳子”),在很多细菌中都存在,甚至,与某些病毒的基因高度一致!更有趣的是,这些病毒往往是专门侵犯这种细菌的“噬菌体”。
看到这里,不知道你是不是跟小墨一样,想到了一个词儿——免疫。就拿我们人体来说吧,身体里面有一系列用来清除外来入侵者的细胞,它们可以记得入侵者的特征,下次再次短兵相接的时候,能迅速识别并加以精确打击。我们熟悉的很多疫苗,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将减毒灭活了的病毒或细菌注射到人体,它的攻击性已经没有,但是人体内的免疫机制可以记住它抗原的样子,产生抗体,当真的病原体入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识别并清除它们。
而细菌保留了病毒的基因片段,不是正好有点像我们人类免疫系统“记住抗原的样子”这个环节吗?会不会这种CRISPR就是细菌的免疫系统呢?

这种猜想很快得到了证明。在研究酸奶的发酵菌——嗜热链球菌的时候,人们发现,将这种CRISPR序列导入细菌,可以让它抵挡某种病毒的入侵。
那么现在摆在刨根问底的科学家面前的问题就变成了——CRISPR怎么就能靠这么一段小小的序列完成免疫这么大的事情的呢?
又经过了漫长的探索,这种机制被科学家解开了。原来,这些CRISPR序列也是可以表达成相应的RNA的,这些RNA平时的工作就是拽上一种叫做cas的蛋白,在细胞里巡逻。只要他发现和自己可以完美匹配的DNA,他就会抓住,然后让cas蛋白把这段DNA切碎。说到这里,聪明的你也一定发现,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对基因动手术的两个工具——GPS定位器和剪刀。没错,既然你都想到了,科学家更不会放过这个像上帝之手一般的疆域。
2013年,三个实验室分别都证明,CRISPR RNA序列和cas9蛋白强强联合,居然可以用来编辑人类的基因组。这三个研究组分别是女科学家杜德纳和卡朋特组合、麻省的华裔科学家张峰、以及张锋曾经的老板乔治丘奇。这层窗户纸一旦捅破,各种惊人的进展在极短的时间内纷至沓来。在科学家的手里,cas9蛋白变成了一个万能的卡槽,一边可以插入CRISPR RNA,另一边可以插入目标DNA,只要RNA和DNA匹配上,cas9就咔擦一声把DNA剪断。甚至,这个卡槽还可以升级,可以同时插几条RNA,同时寻找好几段DNA序列进行剪除。利用这个高效的工具,理论上可以无所不能,实现对特定基因的表达调控和修饰。
科普博主鬼谷藏龙曾用过一个比喻,来形容这种可怕的技术:我们原本知道有一个野外部落可以砍树,然后有人发现原来他们有一群叫做樵夫的人,这群樵夫会根据一些谜之指令来到某棵具体的树前面,用斧头把它砍倒。使用CRISPR/Cas9来编辑基因,就是成功地操纵这个樵夫去砍了自己想砍的树。再后来,人们搞明白了樵夫的行为模式,然后拿走了樵夫的斧头。樵夫依然会根据命令走到某棵树前面,但是不再砍树——我们给他一把凿子,樵夫就会在树上凿个洞;给他一把刷子,他就把树给涂上颜色;给他一把刻刀,他能给你雕出花儿来……

既然无所不能,资本市场必然异常敏感,几家商业机构迫不及待布局CRISPR,争夺它在农业、医学等方向上的潜在价值。围绕CRISPR/Cas9技术在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医学等各个领域的应用,杜德纳和卡朋特组合代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张锋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布德罗研究所展开了耗时几年的专利大战。2017年2月,受全球科学界瞩目的CRISPR专利之争终于尘埃落定,美国专利和商标局(USPTO)维持原判,将真核生物环境中的CRISPR专利权判给了布德罗研究所张锋教授的团队!判决当天,张锋的爱迪塔斯医药公司股价大涨30%。2018年9月,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宣布坚持美国专利商标局先前的决定,这场旷日持久的“专利大战”落下帷幕。
正当世界上科学团队你追我赶的时候,中国的科学家也不甘落后。2016年七月,中国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第一个吃起了螃蟹。华西医院的卢铀教授团队宣布开展全球首个CRISPR人体试验。使用革命性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 Cas9编辑癌症病人T细胞并回输到病人体内进行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
我们知道,T细胞是人体的免疫细胞,它的角色是人体的巡逻兵,发现异己就予以打击。T细胞之所以能发挥这种功能,这是因为不同细胞表面有不同的蛋白质,T细胞就是靠着这些细胞膜表面的蛋白质去鉴别细胞。本来,T细胞鉴别到癌细胞后应该使癌细胞自动裂解,但是癌细胞太狡猾了,它可以在表面产生一种叫做PD-L1的特殊的蛋白质,PD-L1和T细胞表面的PD-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是一种重要的免疫抑制分子,相当于T细胞免疫反应的“刹车”)结合,令T细胞“耳聋眼花”,认为癌细胞是“无害的”,战斗力大大降低,癌细胞得以逃出生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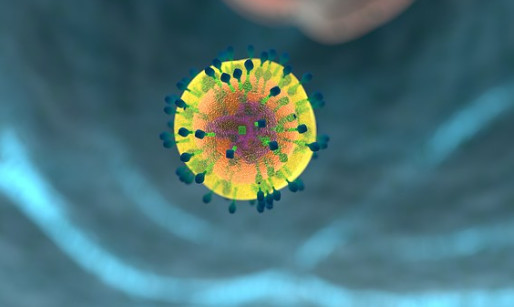
卢铀教授带领的研究小组从患者的外周血液中提取出T淋巴细胞,然后用CRISPR/Cas9技术敲除PD-1基因,恢复T细胞的抗肿瘤能力。经CRISPR编辑后的T细胞在实验室中扩增后,再回输到患者体内。研究小组希望,借助淋巴细胞在人体内的流动,经过改造的T细胞可以经过血液循环能够回到癌症部位发挥作用,攻击并杀伤癌细胞。
小墨相信,新生的基因编辑技术一定有很多不完美、很多的局限,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需要科技界、工业界、医学界、公众和媒体的审慎对待,但是小墨还是难以抑制地感到激动。在人类和大自然相生相克的百万年时间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可以对上帝在遗传密码上的笔误说“不”,我们不一定要被动接受各种与生俱来的病痛和折磨,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存在于这个星球上的方式。也许,从千百万年的时间尺度看过去,人类躲避不了必然的宿命,但是,当你看到饱受遗传病折磨的家庭和个体可以更加长久轻松地生活下去,你也不愿意去阻挡基因探索的脚步,不是吗?
文中图片来源:https://pixabay.com/